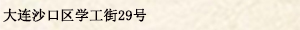作家人气榜薤村十日陈应松
县城通了火车,这是他进去后才有的,感叹时代变化太快,他要把这三年半的损失补回来。但县城火车站是新修的,空无一人,两边是菜地。走出站,有几个“摩的”。问一个老头去薤村多少钱,那老头竟说不知道。仝大喊告诉他就是种意杨的那个村。半天才把意杨说清楚,就是意大利杨树。“噢,杨树,全县都种杨树啊。”这老头是个聋子,还神志不清,坐他的车危险。走了几步再问,有汽车直通薤村,有班车啦。他很兴奋,坐上了一辆破公交车。车上的人一个都不认识,都垂头丧气地想自己的心事。司机也不知为何很烦,到了一个村就吼说:××村下车了!快点,想在车上过年呀!一干人马提包携裹地慌张往车下跳。救火去似的。
是冬天,初冬。庄稼没了,但田野壮阔,村舍岿然,鸡鸭的叫声和狗的奔跑都坚强有力。我是回家来的,他说。看到水渠中的倒影好新鲜,一漾一漾的,突然想起在电脑上进行网络学习、考技术等级证的同改,他们还在监狱里,也许准备吃晚饭了。现在,他也要在电脑前点击“浇灌”,于是所有喷灌设备就自动开始工作。喷灌时大棚的水雾会出现彩虹,那是非常神奇的。
河。河堤和树。意杨。那么多意杨。他没有饥饿感。倘使在三月呢,满是油菜花的堤坡,像瀑布一样漫向四面八方,一望无涯。现在,田野依然美丽,因广阔坦荡而美丽,美丽是一个巨大的心灵震撼,美丽不是小眉小眼,荒凉也是美丽,譬如现在,此时此刻。还有房舍、楼房,做得越来越好,欧式的设计,欧式的门窗,多讲究呀,还有人家门口的汽车。我应该有的。我一定会有!拐了两个水湾,越过一片枯死的芦苇荡,就是薤村。芦穗在空旷的寒野弯腰摇摆,一蓬蓬苍耳和野蓼在田埂灰头土脸的。还有荻秆,高壮胆大。电线杆和电线像拉皮尺的土地丈量员在分地。路边的包菜鱼鳞一样闪着亮光。喜鹊窝摇摇欲坠地挂在纤细的意杨上。路边有小伢们燂野火焚烧的痕迹,黢黑残破。水草有青有黄,野猫湖的枯荷浩荡向前,或站或欹,把下午的天空都抹黑了。
老房子只能是老房子,草垛无人收拾,估计里面成了黄嘎郎子(黄鼠狼)窝。几棵橘子树上还挂有橘子,被鸟雀啄空了。有人喊他的老婆卞如花。卞如花有肥胖症,鼠眼贼圆,走路哮喘,整天气吼吼的,好像谁都欠她八吊钱。仝大喊当初找这个胖女人,可以顶他或者他娘他姐两三个,像一截千年乌木。彩礼还花了五六万,不还价。村里人说,大喊,你咋找这么个胖子?仝大喊说,就是称肉也划得来。人家说,大喊你又不是娶回来杀了吃的。大喊说,就是杀了吃的。可这女人生性暴虐,爱惹事,常扇他耳巴子,还拿大奶甩他。他有时候睡在大奶上,就像睡在粮堆上,有殷实感。胖女人给他生了个肥瘦适中的女儿。但大喊在与邻居吴二瓢争一个门口的粪坑时,把吴二瓢打断了三根肋骨加别的伤,比如卵蛋挫伤,定为轻伤一级,就去坐牢了。那时候,他时常发闲,不喜麻将,就在门口抠着脚丫子看风景。监狱里服刑没事,也在大棚门口抠脚趾,那就是神仙。家虽然房子不好,但后门是秧田,吹着穿堂秧风抠脚,门口有喜鹊白鹭,水青岸碧,有几棵苦楝,躺在树荫下打鼾,还有什么比这更美的?树都是野生的,无论在门口和水边,都恰好长在该长的地方,不像现在,人为划行栽树,看起来整齐漂亮,实际上没一点卵意思。乡村就是自由散漫的,树是自由散漫的典型代表。
“我一有酒,你就回了。”老婆喘气说。老婆还是那副死胖样子,提着酒,也不知道是给哪个男人喝的。她说是打麻将一个老头输给她的,今天手气好。“老子十打九输,你一回来老子转运。”她说。她又说,“哪个婊子养的亲热老子,老子有酒把他喝?喝了翻瘟去死的!”
仝大喊耳中听着这些叮叮嗡嗡的咒骂声很亲切,就像昨离今回。他的身心一下子就回到了村里。
“村里有人字拖鞋卖么?”他问老婆。
“你要死呀,这么冷的天买拖鞋?洗澡又不是没有拖鞋。”
他就去买拖鞋。家里没有了他的鞋子。他买凉拖鞋,人字形的,吊儿郎当、油子哥儿的那种。他渴望那种。
“垄上公社连锁小超市”。秋秋家的。秋秋过去就开小卖部。现在的小超市什么都有,好像还是卖品牌。还卖棺材,门口有棺材,黑漆漆的,一口价,三千八百元,有牌子,有条码——“曹氏棺材”。日,这还小超市咧!棺材铺!
总之,琳琅满目。他给小婧买了两包垃圾食品,还买了一块肥瘦相间的肉,有老婆赢来的酒,必须配上肉才有味,今天开酒戒!
他想和吴二瓢瓢哥喝一杯,那日子就回来了。过去他与瓢哥关系很好的,一翻脸就成了仇人。可是他怀念与瓢哥一起喝酒的日子。瓢哥早搬走了,去县城了。
老婆让他去学校接女儿小倩。
仝大喊进学校门就被拦住不让进,问是干什么的,仝大喊说是接小伢。但守门的老头眨巴着眼睛对他从上看到下,这让仝大喊明白他没有换衣,穿的是监狱里发的衣,他穿习惯了。是那种蓝色的棉袄,前胸和背上有一些特别的竖条纹的,就是囚服,还有囚头,头发没有长起来。他胡乱找了一下,没找到过去的棉袄,也就忽略了。“到外面去等。”继续切菜的守门老头挥着菜刀说。
这很不吉利。按说,出狱当天是要换新衣服的,或者戴个假发,叫重新做人,还要在宾馆住一夜,以去掉晦气。他没想有这种讲究,同改还提醒过他。
很多人都进校园里去了。他趁老头不注意,也就混了进去。他发觉衣服穿得不对,接下来出了更大的问题。当然,他可以戴一顶帽子。不过他都忘了。
放学就是放一群疯子出来。他在二年级门口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女儿,每年女儿都会跟着她妈去探监。最后一年没去,去年他的地就没了,这是他不知道的。
“小倩!”他喊。
这伢,衣裳没扣好,书包没背好,跑出教室就听到一个陌生的中年光头男人在喊她。她站了一下,又准备跑,但被仝大喊一把抓住了。难道她真认不出我了吗?监狱的床头有张亲情寄语连心卡:“爸爸,我和妈妈等你回来。女儿小倩写。”那歪歪扭扭的字难道不是我女儿一笔一画写给我的吗?仝大喊好一阵伤心,这就把小倩抓得更紧,生怕跑了或者飞了似的。小倩好像被抓疼了,“呀”了一声。不过女老师早就盯住了他,一个穿囚服的陌生男人。责任感让女老师挺身而出,勇敢地把他和仝小倩隔开:“你是接哪个的?”
“仝小倩呀。”
“你是她家长吗?”
女老师的眼睛非常毒,长着一张梯形脸,两只眼睛像安在脸上的监控摄像头,鼓着高分辨率的强光,“我怎么不认识你,我认识所有家长。”
“家长还有假的吗?小倩,我是你爸爸,你妈要我来接你,你不认得我了?”他俯下身对小倩说。
小倩却摇摇头,一脸的困惑,往梯形脸老师怀里挤。但仝大喊分明感到是老师的那只长指甲手把他的手掀开,尖尖的指甲把他抠裂了一块皮。他看时有紫钳印和血痕,下手狠啊!此刻,他讲话时希望找一个证明人,可惜他没找到,这是两三个村的学校,接小伢的全是老头老太太。有一个面熟,又记不起老头的名字,姓也忘了。“哎……您郎嘎好,我是大喊……”他又用手示意,但手语不清,显得慌张。那老头看他囚服,还有寒光闪闪的光头,拉着孙伢闪了。
一个犯人会让整个学校打寒噤。狗东西,探监见面那么会喊爸爸,今天不会了?
“我是你爸爸,小倩!”他声音放重了,甚至想跺脚。
小倩被这个男人粗壮的嗓音吓傻了。警觉敬业护犊的女老师赶快叫来一个男老师,他被拉拉扯扯弄到一间办公室里,有几个人看着他。他摊开手两眼发怒:“我、我干了什么?我接小伢的……我叫仝大喊,我的女儿仝小倩,是薤村三组的……”
他怎么说也没用,现在要一个人来证明他就是仝大喊,是仝小倩的父亲,是坐牢回来的。求他心理的阴影面积吧。他的汗都要下来了,而且是滚滚而下。这个季节,他还奇怪地穿一双人字形拖鞋,这是个什么人?越狱出来的?他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。
围上来的人就像看一个怪物,看一个小偷、人贩子。那个女老师的梯形脸上好一副大获全胜的表情,那张脸难看死了,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脸。你这丑老师说家长都认识,就不知道仝小倩也是有父亲的,有个即将服刑期满的父亲?好在他终于在人堆里用眼珠子扒出个熟人,就是村里的前任村主任文爹。文爹很消瘦,很干净,始终穿中山服,头发梳得一根不乱。是有人找到的,看认不认识你们三组的这个人。
“噢,大喊。”他说。他点头。
这事就解决了。他就领女儿回家了。他有点生气地扯着小倩走。回头看了下木杆上高高飘扬的旗帜,好难受。
“连老子都不认识了么?跟妈妈去看过老子那么多次,个臭狗日的!”他骂背上的女儿。
认识的人出去的太多,也死得太多。几年好些新坟,也不知是谁的。好像村里人也不关心这些,把一个死人埋了,这个人就处理完了,大家都接受,不再哭泣。世界是由许多活生生的人轮流转的,转到哪个头上死了,就钻进土里去睡一万年,都很公平,都不吭声,一人死一次,所以田野比学校安静。学校的老师你们把人间问题都没搞清楚,办个么屄学校唦!
瓢哥的菜园子就像火葬场,好恐怖。他只想跟瓢哥喝酒。瓢哥报的是民事案,让大喊赔他几个钱了事。可瓢哥的亲戚不愿意,说还是让他坐牢,兴许死在牢里呢。这话是当时的副乡长曹炎告诉他的,听说现在是乡长了。曹炎是大喊老婆卞如花的表哥,这案子他帮过忙,也送了他不少。大喊为人冲动,激动起来说话是喊的。父母取什么名字,长大就是什么人,乡下有这种说法。后来报了刑事案,这事就成了。瓢哥村里待不住,就去县城拓锅盔卖;他老婆往面里包肉,擀面成形,刷油,瓢哥就往炉膛里贴。这几年,锅盔涨价,从他进牢里时两块钱一个,变成了三块五一个。春节五块。听人说,现在锅盔越做越薄,是放了明胶,所以再薄也扯不断。如果是工业明胶,就是回收的塑料鞋底做的,就等于是吃破鞋底。恶人有恶报,因为卫生不佳,包死猪肉,又被城管砸过好几次炉子,放塑料破鞋拓锅盔的瓢哥就跟老婆有荣分居了,有荣在超市扫地,他捡荒货。
晚上独斟独饮。吃辣椒,吃大蔸果和酱萝卜。监狱里天天吃鸡骨架。鸡骨架萝卜汤、鸡骨架番茄汤、红烧鸡骨架,鸡肉呢?警察和守法公民吃了。
他问戚妈的坟还在没,后来他拿着一杯酒去找坟。是与瓢哥家交界的标志,坟包很小,过去就是用草垛盖住的,现在还加上棉梗。问题是,瓢哥将养母葬在两家分界处,也不犯法,只是让仝家人瘆得慌。这是结隙的开始。好在瓢哥没对养母感恩,坟没培,一年一年小了,长着一些苍耳、狗毛烧,也就看不到了。不挡也没事,看久了就习惯了。人鬼共居是乡村寻常景色,魂幡飘摇也是田野风光。坟就是一个土包,人死骨头烂,还能有什么?
仝家吴家谁先来此居住,说不清了。房子都修过,屋界也没细分,之前都住杂草里,土坯房。就算砖瓦房,譬如瓢哥的房子上了锁,几天就锈了,门缝很大,窗户也破了,黄嘎郎子钻进钻出,门口全是狗尾草和蒿子。狗过去一趟,沾了一身奇怪的臭气难闻的什么果实,疼得哇哇叫,走路歪歪倒。门板像是涂了牛屎,像畜圈的门。
祭完戚妈,找棉袄、帽子,都有了,帽子印有“野猫湖农村信用社”的字,很好。可是心里是对那个梯形脸女老师的愤懑,“你说,小倩这么矮的个子咋让她坐倒数第二排?”
“夏天墙旮旯里全是夜蚊子,咬得大疱小疱,不是我送几次瓜还调不到倒数二排,坐老后一排。人家有钱的送韩国爽肤水防晒霜……”
“臭狗日的!”
趁着酒意上床,老婆卞如花一上来就咬住他的下体,像吃冰棍似的发出噗嗞噗嗞的吮吮声。再骑上来就摇。这一座山把他压的。卞如花下身像沙漠,口里有气味,还没射精就开始想监狱。老婆翻下身来喘着气厚颜无耻地问:“梦见过老子没有?”仝大喊想死的心都有。
“……你晓得二瓢家是怎么搬走的么?”老婆得意洋洋地告诉他,“老娘天天朝他门上泼粪。哪个叫你把老子男人搞坐牢的……他不是又生了个女伢么,三个月,老子就朝她嘴里塞花生……”
“你要杀人啊!”仝大喊跳下床来吼。
“去你娘的!老子拿你没办法,你改造得像无卵太监了,看来还是得坐几天牢……”
这么报复人家三个月大的婴儿,不是畜生不如?瓢哥比他小,都这么叫,连他养母也这么叫。养母可怜,生下八个伢,一个没活。她丈夫吴爹在镇上挑“八根系”,码头工人,常常回来扁担上挂一副猪心肺。有了心肺汤,肯定叫他们姐弟去喝。但戚妈吃得好,却不会带伢,有两个伢是在月子里被棉被压死的。一对双胞胎,聪明可爱,七八岁时,一个发病,另一个也在家发病,两个同时死了。听妈说,戚妈在田里车水,带去的一个在田边玩,突然高烧,口吐白沫倒在田埂上。家里的一个也突然高烧倒地。背老大回去,两个伢一会儿就没气了。戚妈丈夫后来也死了,就她一个人。对大喊他们姐弟很好,视同己生,到她家去就跟自己家一样,有什么好吃的都给大喊他们吃。听说大喊一两岁时还是她带的。每到春节,大喊妈就把她接过来,在他们家吃团年饭。她也不会空手进门,提几包酥食给仝家孩子,还有一块两块的压岁钱。她手上有戒指,腕上有镯子,耳上有耳环,还悄悄给了大喊妈一个玉镯子,镯子里面有一条龙。有一次大喊家失火,大喊妈在田里做事,把大喊锁在家里,是戚妈将门踹开,救出了大喊。说白了,大喊这条命,是戚妈捡来的。他和他姐“出肤子”(麻疹),娘下地干活将他们锁在家里(总是锁在家里,怕在外头出事),他们发烧,眼睛肿成一条缝,又渴又饿,扒着窗户哭喊,是戚妈从窗户外给大喊姐弟吃的。还有犯痄腮时,戚妈给大喊用母牛尿煮了五个鸡蛋,先在鸡蛋头上用针戳几个眼,鸡蛋熟了,吃了就好了。后来,村里人看戚妈孤苦伶仃,在镇上捡了个豁嘴伢儿给她作伴,就是二瓢,瓢哥。长到读书年纪,戚妈将瓢哥带到荆州,将豁嘴缝上了,可讲话还是听不清,呜呜囔囔的。后来读书不行,就给他找了个媳妇,敲锣打鼓娶进门。戚妈什么都给了瓢哥,临死时瘫痪在床,天天头疼喊叫,喊得下巴都脱臼了,医院,就这么死了……
(摘自《北京文学》第10期,阅读全文可点击文末北京治白癜风好北京最好白癜风医院治疗偏方
|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