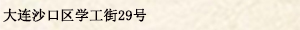杨春峡谷四季
峡谷四季
文/杨春
我登上白杨河大峡谷一处褐然如血的山岩,立即有一种奇怪的感觉:这山岩的形状像一口倒扣着的不规则的铁锅,四周嶙峋,缓地倾斜,顶部略平,矗立着几块很大的灰石头――仿佛几只石龟趁着夜色爬到来这里望月,又仿佛天上落下陨石聚集在这里开会。山岩的地势如此之高,登上远眺,整条白杨河大峡谷尽在眼中,适合坐着休息吹风和冥想,最适合的是站在上面看风景、拍风景。
这是一条一望无际的峡谷,放眼望去,看不见峡谷的源头,也看不见峡谷的终了,峡谷两岸山岩褐然如血,宽处不足百米,窄处仅三十四米。发源于西部乌尔喀什尔山的白杨河,自西向东曲折蜿蜒汇入艾里克湖,白杨河蜿蜒,绕山脉,走戈壁,满眼的黄沙飞石,而当流径大峡谷时,白杨河如一个返老还童的男子,换发了青春:两岸的山岩为它遮蔽了风沙,聚焦了雨露,胡杨林、红柳丛、芦苇荡四季变换的色彩是最自然美妙的装饰,汲水的羚羊、野马、野兔等野生动物则是峡谷跳动的音符。
因为有着在乌尔禾工作生活的经历,白杨河大峡谷成为我经常探足的地方,这处可登高远望的山岩,成为我休息、眺望、吹风、冥想的最佳去处,以龟形山岩石为据点,我拍到了峡谷四季的景色。
春野趣早春,去大峡谷踏青野炊是克拉玛依人亲近大自然的最佳选择。
新芽的胡杨林是峡谷最悠长的风景,我坐在山岩之上,两个哈萨克青年在我视线下的河沟玩耍,女孩脖子上系着花格子围巾,脸颊红红的,女孩在给自己男友助威,小伙子则捡了碎石丢水流,我听不懂哈萨克语,但从他们的欢歌笑语,从他们星星一般明亮的双眸中,我看出他们的快乐。
午后的太阳从头顶照下来,温温暖暖的,像手指在衣服上拨动,这是白杨河峡谷早春的阳光,泥土的湿气在阳光下缓缓升腾;这是峡谷最欢乐的时间,鸟鸣在胡杨林里箭一样飞行,每一声鸟鸣都像鸟儿向着空中吐出一支欢快之箭,我坐在山岩上,聆听着鸟鸣声像密集的箭一般齐飞的奇异时刻。
蒙古老人旗满是野饮的主厨,他指挥着年青人在地上挖一个大坑做炉灶,从河沟中提出清凉的白扬河水淘米洗菜切肉,还用胡杨枝做了一把整齐的筷子;小河潺潺流淌,几个女孩踩着河水中随处可见的黑石,洗着新鲜的黄瓜、辣椒、皮芽子和西红柿,那是预备做皮辣红的原料,皮辣红是新疆菜系中清爽可口的凉菜,也是戈壁野炊中常备的凉菜。
旗满师傅在做抓饭,他神情专注,一招一式极为讲究,好像在酒店的高级厨师做着佳肴。他的身后,新芽的胡杨林中,铺开的大布单上,摆放着馕饼和碗筷,有人沿河采来野花插在瓶中,最芬芳的是一束早开的沙枣花。
当我跑下山岩,河岸边已燃起了篝火,热腾腾抓饭已出锅,香气袭人的烤羊肉滴着垂涎,还有黄瓜、苹果、西瓜,还有啤酒和烧鸡,当人们又吃又喝,酣畅淋漓之际,埋在火堆里的红薯、土豆又熟了,外焦内软,香香甜甜,旗满老师给了我一颗烤土豆,我蹲在篝火旁,剥开红薯皮,热呼呼地大吃大嚼,直吃得满手满脸都是黑色,像一只花猫那样的贪嘴。
酒足饭饱之后,音乐响起,朋友们围着篝火跳起快乐的免子舞、维族舞,我在其中蹦着跳着,心里充满了快乐。那天,野炊的人们一直玩到夕阳西下,大家遵守着户外公约,齐心动手,灭火收拾餐具,弃物打包,收拾了一天快乐的心情,踏上归途。
夏清凉盛夏,克拉玛依酷热难耐,白杨河大峡谷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,善于经营的乌尔禾人,在峡谷景区预备了纳凉的帐篷和丰富的餐饮,还因地制宜开设了漂流等娱乐项目,人们穿上救生衣,推皮筏入水,顺着清澈水流前行漂移,享受着紧张、惊险的沁凉和舒爽。
我的山岩距离峡谷景区较远,听不到人们欢乐漂流的声音,却能看到河谷之内牧羊人的蒙古包。峡谷是天然夏季牧场,山岩之下的峡谷景色,胡杨苍翠,芦苇纵深,水鸟纷飞,洁白的蒙古包坐落在河谷浅滩,或者隐秘在胡杨树中,那是牧民的家,有放牧的骏马、摩托车和牧羊犬,成群的羊在胡杨林中悠闲地吃草,偶然能看到黄羊在河边汲水――这些都是我愿意摄入镜头的峡谷景色。
七月,一个晴朗的夏日,我和摄影人艾力登上山岩远眺望,我们看到一匹枣红马在胡杨树林纳凉,就跳下山岩去看马。
一缕缕阳光从树叶缝隙间漏射下去,给枣红马蓬松的鬃毛上添了许多小小的明亮的斑点,在那棵树上,两只大鸟吱吱喳喳地叫着,带着悠然自得的好奇神气在它们那空中住宅聊着天儿,我们走近枣红马,却不见马主人,我们决定沿着河流漫游,寻找牧人的蒙古包。
我们在河道里走了很久,峡谷中到处是一串串淡紫色的野苜蓿花,一朵朵金黄色的蒲公英花,红白蓝紫,斑斓悦目的太阳花。一个个矮矮的树墩已经发了黑,四周围长满细细的、光滑滑的枝条,这些新生的胡杨枝条不足一米长,它们将在时间的条河中成长为峡谷的主角。艾力摘了片树叶放在嘴边吹出好听的哨声,他一边走,一边用木棍搅动着脚下的草丛,弯腰拾几只新出的蘑菇,又采一把嫩绿的野菜――蒲公英、灰灰菜、野芹菜、野苜蓿、野葱、还有茭蒿,这些我熟识的野菜令我兴奋,也跟着采了一把又一把,背包塞满,又把外衣的袖子打了结,塞满野菜搭在肩头。
一段狭窄的河道,我们看见一些胡杨树快活地横躺着,根在这边,树梢却到了河岸那边,它们有的枝繁叶茂,好像在水中鞠躬,有的已枯死,树干上新生着苔藓、缠绕着绿色的藤蔓。我们预备通过横亘两岸的一棵老胡杨的粗大树干爬到对岸去,艾力很快过去,而我爬到一半就不爬了,我坐在胡杨树干上,脱了鞋,两脚在河面上快活地踢浪花。这时,我看见两只戏水的水鸟,它们不时跃上河水中的石头,再从石上跳入水中互相嬉戏,看到人来,它们又一个猛子扎入水中,立即不见了踪影,不一会儿在十米开外它们又浮出水面,沿着河流前游,在它们的身后划出两条长长的水纹。
蒙古包搭建在两棵老胡杨的树阴下,背倚红褐色的山岩,前方是奔流的河水。我们在蒙古包前看到一个正在打瞌睡的哈萨克老妇人,我们走上前叫醒她,没有因为搅扰了妇人悠长的夏梦抱歉。
我们喝了奶茶嚼了馕饼,又把采到的蘑菇和野菜摊放到阳光下晾晒,晒干后的绿色山野菜将在冬天的热水中重新焕发生机,炖或煮都能给我们提供美味和营养。然后,我们和老妇人一起坐在蒙古包前的胡杨树下乘凉,峡谷之外的戈壁滩,酷热正席卷着大地,峡谷内却因河流,因树林,因穿峡而过的微风有着凉爽和舒适。
我们在胡杨树下乘凉,微风时而吹动,时而停息,有时忽然直冲着脸上吹来,仿佛风要大起来了――周围一切都快活起来,摇晃起来,动起来,草木的梢儿娉娉婷婷地摆动起来。我正高兴着,谁知风又停了,一切又不动了,只有夏虫被惹火了似的,齐声叫着,那些叫声倒是和盛夏的午后相配,仿佛那些虫儿也为找着一个避暑的好地方而欢庆。
秋斑斓九月里一个晴朗的日子,我在白杨河大峡谷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散步,从景区大门入口,沿着河流一直向东走,这是一段走熟的路,我将登上最高的山岩俯视峡谷秋色,还将在浅滩处的蒙古包休息片刻,喝一碗老妇人煮的奶茶。
我斜跨着相机,预备着随时拍摄,秋天的峡谷色彩斑斓,蓝天白云配合着变幻莫测的光线,胡杨树叶黄得那么耀眼,河水流淌的那样畅快,树林里尽是欢唱着的鸟雀,如果不拍摄自是辜负了好时光,辜负了峡谷好风景。而实际情况是:我登上山岩拍了几张峡谷全景,将满谷的秋色尽收眼底之后,就不再管拍摄的事情了,我忙着采摘,还有收集。
我在山岩的下方看几丛匍匐着的野葡萄,果实已完全成熟,一些被鸟雀啄残,一些落在地上,一些被阳光晒干,只有少数一些闪着紫红色的莹亮的光,颗颗都有牛眼那么大,而且色泽动人,芬芳袭人,我想法摘了那些果实,吃得满嘴发紫。
又有几丛野石榴树丛站在河对岸,密密麻麻、星星点点,红灯笼般的成熟果实在秋风中招招摇摇,我踏着石头跳过因为秋天消瘦慵懒的河流,野石榴只有小拇指那么大一点儿,只有皮能吃,有点酸甜又有点苦涩,我像嚼果丹皮一样吃了许多。我又采摘到了黄金的铃铛刺种子,粉红的野草莓、黑而剔透的沙枣,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又知道能吃的植物果实。
我还留意河道里飘着一片片落叶,黄红绿三色杂呈,在水光剑影中显现出奇异的色彩,我急忙打开镜头盖,在这秋光斑斓的色彩中翩翩起舞,拍摄之后,我还为着落叶的前程操心:不知哪片树叶做了蚂蚁的渡船,也不知哪片树叶要被鸟雀衔去垫巢。
秋天是水量最小的时候,水位远远地从河岸退下,可以看到胡杨树下被河水掏空的根部积满了落叶,那些树根优美繁杂地盘绕着,高高地露出地面,我总觉着里面会是某些野生动物的家园,那有着美丽毛皮的小动物会突出现在铺满金色落叶的河岸上。
我傍晚十分才来到蒙古包,这家牧民做着转场的准备,除了老牧人夫妇,还有两个青壮年男子在浅滩上忙碌着,门前停着两骑摩托车,还有一辆天蓝色的客货车,一些家什已装进车斗,另一些也打包成捆,羊群还在埋头吃草,羊们也知道,只有在这里吃得膘肥体壮,才有力气行走几百公里去冬牧场,到第二年春天再转场到峡谷夏牧场。
午后,我仰面躺在一片厚厚的落叶之上,欣赏着金黄的树叶在明朗的,高高的天空中的静静地变幻,我看到一只小松鼠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。啊!在这新鲜的空气中,在深秋明朗的天空中有鸟雀在歌唱,那清脆的声音像银珠儿一般从空中纷纷撒下,我想,那鸟雀的翅膀上一定带着露珠儿,因为那歌声似乎是雨露滋润过的。
在欣赏了一会四周的景色之后,我便睡着了,这样甜蜜又安稳的睡眠只有喜爱大自然的人才能领路到。
冬映雪那天,克拉玛依下了一夜雪,树上挂着雪松,我提着相机沉醉在世纪公园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美妙图景中,接到摄影人老赵的电话,老赵说:“去乌尔禾胡杨林拍雪松吧?”
越野车在乌尔禾平原上驰骋,追逐着胡杨雪松的足迹,当我发现已到白杨河大峡谷景区门前时,我激动的大喊大叫。
景区没有人声,也没有雪路,我踏着积雪艰难地走到结冰的小河中央,仿佛推开了拉尼亚王国的魔橱,一幅绝美的冰雪童话慢慢在我眼前展开――冰封玉砌呀,冬天的白杨河大峡谷“雾淞沆砀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”,小河边,千百棵胡杨树、沙枣树、榆杨树银装素裹,如巨大的圣诞树错落有致,还有一些树弯腰探身入水,树杆树技担着厚厚的白雪,变成一座两座三座弯弯的拱桥。仿佛一群顽皮的孩子夜里偷跑出家门玩水,遭遇冰雪,一个两个三个来不及跑回,就冻在河面上,单等春暖花开方能舒展腰肢。
在河道边,我拍到一组组雪蘑菇列队团体操的相片,仿佛看到雪蘑菇在大雪中肆意生长的历程,就像草菇、香茹、牛肝菌、羊肚菌这些蘑菇在雨后迅速萌发一样:雪是菌丝,菌胎是溢满河滩的大大小小的鹅卵石――进入秋季后,峡谷中央,幽灵般的白杨河,河水渐渐变小,渐渐萎缩到了河中间浅浅的河沟,鹅卵石露出了水面,冬天的雪一层层落下来,像赋予了鹅卵石生命,洁白的菌丝在鹅卵石上肆意生长,蓬蓬勃勃地长成雪蘑菇。
老赵跑去树林拍鸟,寻找野生动物了。我不忍心打搅雪蘑菇的静思,溜着河道边踏雪而行,我的脚欢喜地踏在最深的沟里,又欢喜地爬上两岸的高地,有时连膝盖也陷进了雪里,有时又坐在石头上,看身后延展的一串串脚印,最后,我登上最高的山岩,欣赏银装素裹的峡谷,欣赏雪松、冰花、雪坡与褐红色山岩形成的奇异景色。一时间,我的心被一阵巨大的欢乐淹过,生命的美,又一次向我呈现。雪封的峡谷,像一个耐人寻味的谜语,被一层白色包裹着,无声无息,又像一个熟睡的美人,做着千年的长梦。
深一脚、浅一脚,我站在了常去的胡杨浅滩,蒙古包已转场去了冬牧场,断绳、碎木、柴木还遗落在那里,麻雀成群地飞来,发出微弱迅疾的声响,它们落在一棵沙枣树上叽叽喳喳,沙枣冰冻在树枝上,成为鸟儿冬天的食物。一只鸟儿显然是鸟群中的勇者,它竟然飞到我抱着的一颗胡杨树桩上,豪不惧怕地啄起树桩顶部的木屑来,我站着没动,它就飞到我的肩上呆了一会,这时,老赵恰好从树林中走来,他举起相机,拍到这一场景,我看着这张相片,感到佩戴任何肩章都比不上这次荣耀――那是鸟雀给予的荣耀,是大自然颁发的勋章。
杨春,女、汉族,七十年代出生于新疆阿勒泰,现克拉玛依市国税局工作。系新疆作家协会会员、克拉玛依市签约作家。发表散文、诗歌、随笔作品见于《中国作家》《青年文学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湖南文学》《草原》《芙蓉》《西部》《伊犁河》《新疆石油文学》《中国税务报》《中国石油报》《新疆日报》《新疆经济报》等,出版长篇散文《戈壁中的大院》,散文集《雪莲花开》。
在场公众平台已经开通原创保护、留言和赞赏功能。
来稿请附上个人简历及照片。
在场
|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