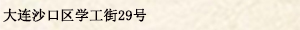风雨舞台下南榆林怀旧六十七
最好白癜风医院咨询 http://pf.39.net/bdfyy/bdfzj/
从南榆林看南山坡和紫荆山的实景近照李万林摄
点击收听本期内容
题
目
风雨舞台(下)——南榆林怀旧(六十七)
文
南坡scsr
图片源自网络
四叔的故事还在娓娓动听地讲述着。东方天际太阳将升的那个地方,正涌集着一团厚重的浓云,云的周边却已是镶满了微淡的霞。晨光送走了暗夜,又在步履沉缓中,迎来了一个明媚的白昼。雾在变淡、消退,最后全集中在以村南白沙泉为源的二道河上空,凝滞在那里,筑成了一道虚幻缥缈的雾纹平流的极浓极浓的雾云之墙。早饭送来了,清一色的高粱面糊糊,如一罐还在冒着热气的黑红猪血。罐子上墩着的碗里,又是清一色的苦菜,墨绿绿乱蓬蓬的,又似一堆宰杀牛羊后切开了的胃里未经消化的残留之物。唯有队长是一罐子黄灿灿的玉米面小米糊糊,里面煮着山药蛋,外加一个令人眼馋,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玉米面窝窝头。此时,初升的太阳正与天边的那团浓云相搏,亢奋欲出,穿透云层,四射出霞光,绚丽璀璨。霞光下的原野,披一层金黄,呈现出一派水淋淋的翠绿。插图:南坡大家争先恐后地向地头放饭担的陈槐古柳下走去。希才大叔最后一个走来,将饭罐端在手里,不急着吃,却是用筷子敲着罐子,望着狼吞虎咽着的人们,用说快板的语调念道:“山药蛋,麻猴猴,茭子面,水糊糊;待说不喝哇,头晕眼花肚饥哩;待说喝上哇,一股一股淌稀哩。”队长脸色阴沉地抢白道:“整日价不知嚼啥X哩,热饭也烧不住你那个X嘴。”干尾巴黄鼬儿不理会队长的抢白,接上希才大叔的话,用戏腔的道白念道:“罢罢罢,休休休,看破世道早回头。”队长白了干尾巴黄鼬儿一眼,半揶揄半抢白地说;“你脸比墙皮还厚哩。你要有那血性,早在尿盔上也碰死了。”二爷饱经风霜的脸上充满了凝重,叹气连连,语气沉缓地叹道:“唉!好死不还如赖活哩,阳世山间疙磨哩。人都是个这!都是个这……”没梁斗不甘落后,急急喝了口高粱面糊糊,又忙忙夹了一大疙瘩苦菜放进嘴里,边嚼边学着希才大叔的腔调,也念了一段:“活也难哩。死也难哩。待说活哩哇,一顿一顿不吃饭;待说死了哇,又怕是贵人多受难。”龇牙狗拦头一棍扫过来:“放心哇,祖上没德,坟园没风水,天生就是‘一顿一顿不吃饭’的命。我保证,贵人轮不上你,还是死了好。要上吊,我给你搓根麻绳绳;要碰死,我给你端个尿盔;要跳井,我把你背到井沿上……”“那可说不来,马粪还有一发哩。”板板历来说话刻薄,这时更来了精神,一语双关地接上了腔:“人是一时一运,哼哼!那东西是一软一硬。十八年还等个薛平贵哩。俗话说:料山料水哩,料不死个人。人要是倒运,喝凉水还塞牙哩;人要是运气来了,走路元宝还绊脚哩。谁能料定咱二兄弟不是个贵人?嗐!说不定运气来了,还真有两天官儿坐哩。”没梁斗明知道板板是在损他,却是不恼,“咳咳咳……”地一阵干笑,自我解嘲地说:“人人都是帝王相,人稠地窄轮不上。”四叔从不参与这类寡话,这时竟也插话道:“二表侄你就放心哇!那还轮不上!你现在不就是一家之长?!铜锁、银桃俩娃,还有铜锁、银桃他妈,都属你领导。家长,家长,一家之长。部长、省长、市长、局长,不也就是带个‘长’吗!你这好赖也还带个‘长’哩,不用急,一个圪台一个圪台往上升。回家喝上茭子面糊糊,出来灌上西北风,你就心宽宽儿等着哇。”众人听了,一阵轰然大笑。笑声惊起了几只鸟儿,鸣叫着,箭一般射向蓝天。一股股湿漉漉的微风吹来,清凉滑润,夹杂着花儿草儿庄禾苗儿的幽香,陈槐古柳下打了个旋儿,便轻悠悠地荡向远方。捎带走了苦菜与茭子面糊糊的酸苦味儿,连同那阵笑声。笑声带走了胸中的郁闷……没梁斗三两口将罐子里的糊糊喝完,又把少半碗苦菜一古脑儿扒拉到嘴里,嚼了嚼,一仰脖子,随着喉头的蠕动,“咕噜”咽进了肚里,撩起衣襟擦了擦嘴,慢条斯理地说:“好我那四表叔哩,我看升倒是升,可不是升官,再过二三十年,睡到棺材里升天哇。咱自己认得自己蛇虫儿(壁虎成龙狗头上长角角哩,没那命也不想望。”四叔古书看得多,受宿命论的熏陶自然也多。在我的记忆里,是个极相信命运的人。每谈起来,引经据典,比古论今,一套一套的理。说到命,便来了精神,拖了说书的腔调,摇头晃脑地长篇大论起来:“二表侄你这话算是说对啦!命是等身的棍,任谁也逃不脱。人常说,命里有五升,不用起五更;又说,命里没一升,早起也无用。人嘛!从你娘肚里‘吧哇’一声落地起,阎王爷早就为你安排好了。王花买了个老子,当了皇帝。咋哩?命就是那真龙天子的命。不是四表叔说你,你是三、四岁上死了娘,五岁失火烧了房,七岁八岁遇上狼,十一二岁放了羊,天生就是疙瘩赖命。”没梁斗却故意跟四叔唱开了对台戏:“四表叔你这话只说对了一半,另一半全错啦。我跟您说哇,不是我命赖,而是我妈搞破坏。”四叔明知道没梁斗爱说些没影儿的话,笑了笑,逗趣似的故意问:“二表侄你这话说到哪里去啦,听了只让人糊涂。俗话说,人世间最圆的是瓜,最亲的是妈。虎毒还不食子哩。你妈不疼爱你也还罢了,咋还能对你搞破坏?”秃狮怪则是将含在嘴上的旱烟袋拿开,吐了口烟,冲着没梁斗歪头瞪眼地骂道:“脚大怨拐孤,拐孤怨腿粗,腿粗怨谁去?尽是些独我理。自己没球个本事,能怨着你妈个啥!快悄悄哩哇,心安安儿地受你那罪哇。”没梁斗不理会秃狮怪的话,满不在乎,怡然自乐,转过头来问我:“表弟,你给咱说说,二表兄这胎面面生得怎样?”跟我相处了几年的没梁斗,我从没认真注意过他的长相,只觉得跟平常人一样,有鼻有眼一张脸。今日这一瞥,我才惊奇地发现,他竟是这样一幅容貌:方脸盘,阔脑门;浓眉,大眼,鼻直,口方;身材高大,体魄雄壮。虽衣衫破旧,面带菜色,却逸溢着男子汉的浩气阳刚,确确实实生就了一副好皮囊。如若穿上一身崭新笔挺的中山装,再有辆小轿车一坐,不知情的人们不认作省委书记省长才怪哩。我的心底泛起热浪,只觉得惭愧、恐惶,脱口道:“好!生得好!!天庭饱满,地阁方圆;方面大耳,虎背熊腰,真乃一副大富大贵之相。”众人又是一阵哄笑。龇牙狗仰面躺在草地之上,架着二郎腿,悠然自得地转着套在脚上的空饭罐,哼了一声道:“啥球富贵相,有点风水,也全从他那个灰X嘴里溜跑了;一副穷相、饿相还差不多。”碧天。蓝、纯、净。白云,稀、淡、薄。夏的早晨,山川万物像从水里捞出来的青菜,鲜、嫩、水灵。田垄间,几只小鸟正在引颈欢唱。龇牙狗话刚落音,长脖儿立刻补了一句:“说塌哇,我看是天生要饭的命,一副讨吃相。”没梁斗回敬道:“娃娃,你是没落花瓣的瓜,还嫩着哩。月毛娃娃结婚,啥球哩也不懂。二哥这命天生好着哩,就是让我妈给破啦,要不咋说是我妈搞破坏?!”“怎破了?”“我妈把我生得低了。”“你怎知道?”“说起来还心酸哩!那是有一年我去关南贩辣椒,在店里遇上了一位算命先生。那先生对我左打量右打量,看得我心里直发毛。我说‘你看啥?’先生连叹‘可惜可惜!’我问‘可惜啥哩?’先生说,‘这么一副富贵相,让人给破了。’我又问,‘咋破了?’先生说,‘你妈把你生得低了。只要好好生在地皮之上,也能家产万贯,良田千顷,使奴唤婢,穿金戴银,前程不可限量;如若生的比地皮高些,就可戴乌纱帽,穿紫蟒袍,妻妾成群,位居极品,贵不可言。只可惜生得低了,破了命相,今生也就只能土里刨食,现打现闹;茶饭粗糙,营生紧造。好与赖比,一天一地。’听了先生的话后,我问道,‘我莫非生到了地皮之下?’先生答,‘正是。’这都是算命先生的原话,我一句也没有瞎加。日哄你们我是个王八。”这话如若出在一个读书人口中,也没什么,但出自一个没读过一天书的瞎汉嘴里,我不由得暗自钦佩。从那时起,也改变了我对没梁斗的看法。他虽终生躬耕于田垄,含辛茹苦地生活着,却并不等于没有天赋与才智。他是时代的弃儿。没梁斗话音刚落,秃狮怪“呱呱呱”一阵怪笑,揶揄道:“日他灰妈哩,日瞎也得有个影儿哩,越说越连个影儿也没有啦。从古至今,谁不是在炕上生娃娃,还能有个地上地下之分?难道还能上天入地不成?!”“唉!这下你可说对了,没上了天,倒是入了地。”“你给众人说说,怎入了地?生在了哪里?”没梁斗诡黠地一笑,说:“我也这样问过算命先生,人家只说我妈把我生到了地皮之下,破了命相。再问,就死活也不肯说了,让我回去问我妈。”说到这里,没梁斗故意卖了个关子,停住不说了。他极悠闲地吸烟,手中的旱烟锅发出细微悠长的呻吟。三小队的社员,都知道没梁斗的话,十有八、九都是假,却又偏偏爱听。人们都在静等着下文,又都故意显出不关心的样子,默不作声。短暂中,一切都沉寂了。乡野上,云影儿摩挲着,四周很静。海娃憨厚,等不及了,推搡着没梁斗问:“究竟问了没有?”“问谁?”“问你妈啊。”“问啥?”“日你妈哩,装啥蒜哩。问你是不是生到了地下?”“问了。”“生到了哪里?”“山药窖里。”“啊——?!”听的人全都傻了眼,表情各异地愣在那里。雾愈淡了,如轻纱般虚幻。祥和瑞气却开始在丝丝缕缕地氤氲蒸升,笼罩乡野,山川便显得缥缈、虚幻,勾勒出一派诗情画意。天,蓝茵茵;云,白生生。故土是母亲,充满了慈爱;故土是少女,显得多情;故土又是壮实的小伙子,强健的体魄中,孕育着不安分的躁动。全因为有这一群人……夏,阳婆儿半茵,四野全是绿。绿野无垠。二爷干桃核似的脸上全是笑意,牵动得那些沟壑纵横的皱纹更加分明,仿佛大西北的黄土地,坎坎洼洼中溢满着古老的神韵。他用手指着没梁斗笑声连连地说:“好小子!好小子!我算服了你啦。真不亏是个没梁斗。我问你,你妈挺着个大肚,不在炕上呆着,干啥去了?怎就能把你生到了山药窖里?”队长则说:“不用听他瞎编,狼吃鬼哩,没影儿。全是些无影传。”这时,太阳已是消退了红晕,变得白灿。白灿的阳光也送走了晨的清凉。露水落了。瑞气便更加汹涌地蒸升。乡野暖烘烘的。风,轻轻的,柔柔的,送来了队里黑叫驴那欢快的鸣叫声。没梁斗望了望众人,见人们注意听的神态,显得得意。他干咳了一声,有板有眼地继续说:“听我妈说,怀我那一年,正闹饥荒。临近坐月子时,又遇了个青黄不接的初夏,家里三天没见一粒粮食。日日糠,顿顿菜。我妈实在饿得挺不住了,下到放过山药蛋籽种的窖里,用手刨那些丢失在土里的,旧山药生出的芽儿上结下的,如扣子般大小的新山药蛋。刚摘了小半碗,只觉得肚痛难忍,一阵紧似一阵,来不及上窖,‘吧哇’一声就把我生到了裤裆里。你们给咱说说,这不是生到了地下,还能是地上?!”插图:南坡
不相信吧,说得合情合理;相信吧,又谁都知道“二金海的口,没梁的斗”。他妈早已去世,已是死无对证。众人的脸上不由得露疑虑的神色,都深深地吸了口气,又在沉思中悠悠地吐出来……
弥漫的晨雾已被朝阳全部逼退。乡野便显得空旷。四周却是浓郁的绿。无边的天空是一片纯净的蓝;广袤的原野上,瑞气氤氲,汹汹涌涌,溶满了夏的绿意,远淡近浓,渲染着故园的山野河川,飘渺中逸现出虚幻。
在以后的日子里,队长曾感叹地说:“这狗日的二金海,不管啥事,只要从他那个嘴里出来,都会编个天花乱坠。死人也能让他说活,胡编也能编得缘缘由由,说出个头头道道来。能谝住人,这也得些本事哩。你要是相信吧,明知他在胡编瞎谝;不相信吧,又说得有枝有叶,有板有眼,人人爱听。管那狗日的真哩假哩,红火热闹就行了。咱庄稼人,满脑袋高粱花子,有球个甚正经哩!”后来我也曾留心观察过,在放过山药蛋的窖里,果然有偶尔遗失在土里的山药蛋。初夏之际,母体已收缩得如一个干核桃儿,然而它生出的芽儿上,结了一串串白嫩却又泛着紫色的新山药蛋,犹如一串串晶莹透亮的葡萄……在人们的沉思中,没梁斗一声长叹道:“看咱这命,说到底,比纸还薄哩,可惜就可惜在生得低了!”这一声感叹,虽低沉,却不亚于当头爆响了一个炸雷,强烈震撼着我的心灵。这叹息声也常拐弯抹角地钻进我那深沉或不太深沉的梦境,伴我终身。先是一阵沉默,再就是“噢!”“啊?”“呀!”的惊叹声。待人们回过味来,在长脖儿一声“生得低了”的怪叫声中,霎时爆发了一阵经久不息的大笑。我记得秃狮怪的笑声最响:“咯咯咯、咯咯咯……”。龇牙狗则是笑得猛一扬腿,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,将套在脚上的空饭罐子踢出老远,传来“咔嚓”一声响,摔成了两半。那笑声,那“咔嚓”声,漫过碧绿如茵的原野,携了些淡淡的晨雾,仿佛正顺着那蜿蜒远伸的古道儿,缓缓地向远方流淌着,滚动着………………各位看官,如果您感觉南坡sr
| |